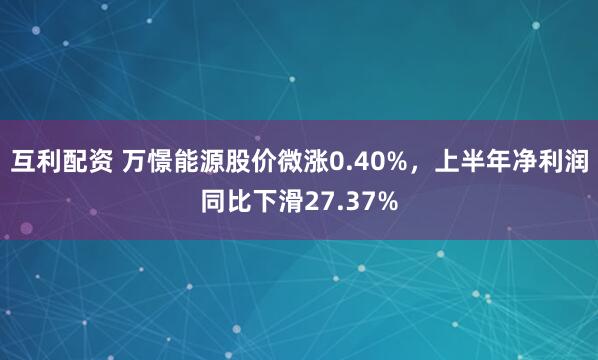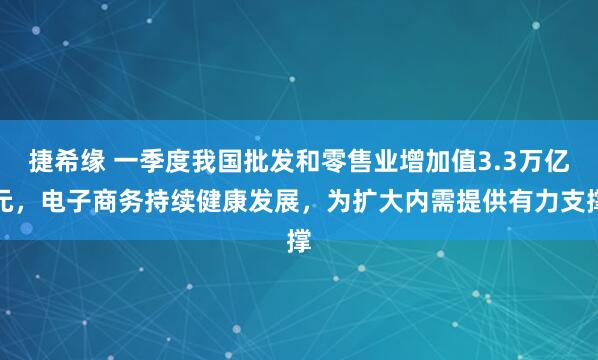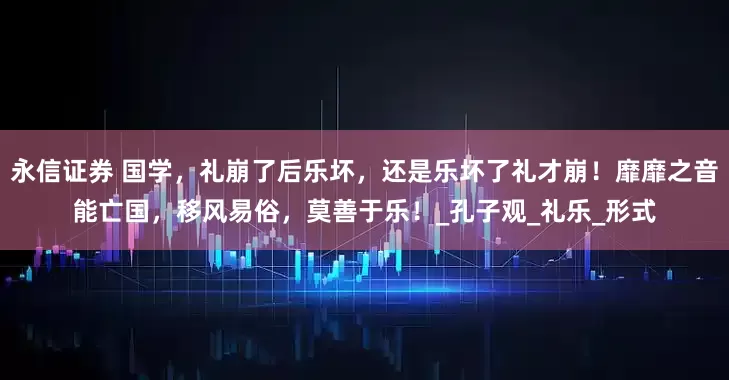
中华文明自周代立制,便以 "礼乐" 为治国之本。《礼记・乐记》云:"礼者,天地之序也;乐者,天地之和也。" 礼如乾刚,确立人伦秩序;乐似坤柔,调和天地性情。二者犹如阴阳二气,共生共荣,缺一不可。孔子观周乐而叹 "尽善尽美",见季氏八佾舞于庭而怒称 "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",足见礼乐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。然春秋以降,时人皆言 "礼崩乐坏",但细究典籍,当明了二者非简单的先后关系永信证券,而是道统崩坏过程中互为表里的显象。
靡靡之音能亡国永信证券永信证券,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!
二、礼崩乃本:制度溃败引发价值失序礼的本质是 "别",即《礼记》所谓 "礼者,所以辨贵贱,序亲疏,别同异,明是非也"。周代宗法制度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,以分封制为政治架构,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传承法则,形成 "天子 - 诸侯 - 大夫 - 士" 的等级体系。礼不仅是礼仪规范,更是维系社会结构的制度性存在。当王室衰微,诸侯 "相王"" 逾制 ",本质是宗法制度的经济基础(井田制)被土地私有制瓦解,政治架构(分封制)被列国争霸破坏,传承法则(嫡长子制)被" 礼崩 "后" 乐坏 ",还是" 乐坏 "后" 礼崩 "?实力取代血缘。此时所谓" 礼崩 ",并非礼仪形式的消失,而是制度性权威的崩塌。
展开剩余76%靡靡之音能亡国,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!
孔子见鲁君用 "郊祭" 之礼,明知 "非天子不议礼",却只能喟叹 "礼失求诸野",正因其洞察到制度性礼统已无法维系。正如《论语・阳货》记载,宰我质疑 "三年之丧" 太过漫长,孔子反问 "食夫稻,衣夫锦,于女安乎?" 宰我答 "安",孔子无奈道 "女安则为之"。这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,而是宗法制度下 "孝" 的价值根基被实用主义消解,制度性的 "礼" 失去了内在的道德支撑,必然导致外在规范的崩塌。
三、乐坏为象:情感表达背离伦理本质乐的本质是 "和",《乐记》云 "乐者,通伦理者也"" 乐至则无怨 "。周代雅乐并非单纯的艺术形式,而是" 礼 "的情感化表达。天子用" 黄钟大吕 ",诸侯奏" 正声雅乐 ",不同等级的乐舞、乐器、曲目,皆承载着" 和同天下 "的伦理功能。当" 礼 "的制度根基动摇," 乐 "便失去了规范约束,沦为权力者纵欲的工具。最典型者莫过于" 郑卫之音 "的流行 ——《礼记・乐记》批评其" 奸声以滥,溺而不止 ""惑而犯节",正是因为这种新兴音乐打破了 "乐统" 的等级规范,以感官刺激取代了伦理教化。
靡靡之音能亡国,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!
季氏享用天子之乐 "八佾",表面是乐舞形式的僭越,本质是对 "礼" 所规定的等级秩序的蔑视。正如孔子所说 "人而不仁,如礼何?人而不仁,如乐何?" 当 "仁" 的核心价值被抛弃,礼乐便成为徒有其表的形式。《吕氏春秋・侈乐》记载,齐宣王 "好滥竽充数",本质是对 "乐" 的庄严性的消解,这种 "乐坏" 正是 "礼崩" 在情感领域的投射 —— 当社会失去共同的价值信仰,任何艺术形式都会沦为功利工具。
四、互为因果:道统崩坏的一体两面从发生学角度看,礼的制度性崩塌是根本原因。周代 "礼" 的维系依赖于 "天命观" 与 "宗法血缘" 的双重权威,当平王东迁,"天命靡常" 成为现实,诸侯 "挟天子以令诸侯",实质是用实力逻辑取代了礼法逻辑。此时 "礼" 作为制度规范已无法约束权力,必然导致 "乐" 的伦理功能失效。但从现象层面看,"乐坏" 又加速了 "礼崩" 的进程 —— 当贵族阶层沉迷于 "新声" 而忘返,意味着他们从情感上放弃了对 "礼" 的认同,制度规范失去了心理根基。
《荀子・乐论》深刻指出:"乐者,天下之大齐也,中和之纪也。" 当 "乐" 不能 "齐天下"" 纪中和 ",反而助长" 侈乐繁声 ",则" 礼 "所维系的" 秩序 "便失去了情感共鸣。这种互动关系在战国时期达到顶点:商鞅变法" 废井田、开阡陌 ",从经济基础上摧毁礼制;同时《韩非子・十过》记载晋平公沉迷" 师涓新声 ",预示着文化层面的伦理溃败。二者看似分属制度与文化领域,实则是" 周道衰微 " 这一历史进程的不同面向。
五、复归之道:重立 "礼乐" 的精神内核孔子周游列国,并非简单呼吁恢复礼仪形式,而是试图重建 "礼" 的内在精神 ——"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?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?"(《论语・阳货》)在他看来,"礼" 的核心是 "敬","乐" 的根本是 "和",若失去 "仁" 的精神内核,徒有玉帛钟鼓,不过是 "礼崩乐坏" 的表象。故孟子提出 "仁政",荀子强调 "礼起于何",皆在重构礼乐的价值根基。
反观当下,物质丰裕而精神匮乏,恰如《乐记》所言 "乐者,心之动也""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"。若社会缺乏" 礼 "的秩序规范与" 乐 "的情感陶冶,便会陷入" 物至知知,然后好恶形焉 "的功利主义泥沼。唯有重识" 礼以道行,乐以道和 "(《庄子・天下》)的智慧,让制度建设蕴含人文精神,使艺术表达承载伦理关怀,方能实现" 礼者为异,乐者为同;同则相亲,异则相敬 "(《礼记・乐记》)的文明理想。
靡靡之音能亡国,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!
注意:辨本末以正纲常"礼崩" 与 "乐坏",实为周文疲敝后的一体两面:制度性的 "礼" 先失其 "序",导致情感性的 "乐" 失其 "和";而 "乐" 的异化又加速了 "礼" 的崩塌。二者非简单的先后关系,而是道统崩坏过程中 "体" 与 "用" 的相互消解。中华文明的复兴,需超越对礼乐形式的模仿,重立 "礼以义起"" 乐由中出 "的精神传统 —— 让" 礼 "成为守护尊严的秩序,让" 乐 " 化作温润心灵的和鸣永信证券,此乃国学对当代文明的永恒启示。
发布于:上海市诚信双盈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